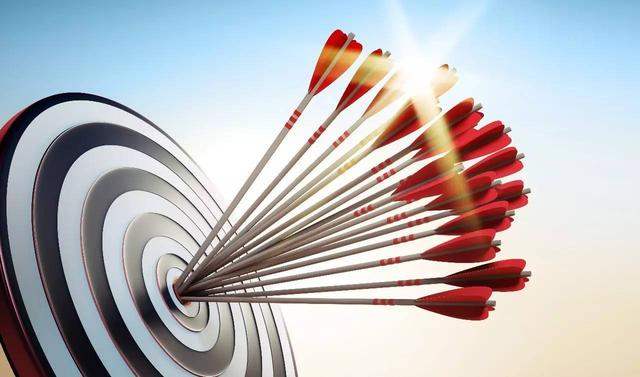解离——沉重的盔甲
南希的《精神分析诊断:理解人格结构》,是非常喜欢的专业书籍…… 书中有介绍心理防御机制,简单理解,防御机制是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在遭到一些主客观的挫伤、刺激时,会使用来保护自己、获得稳定些的自体感的保护机制。 如果你愿意勾勒画面,可以把它们想象成盔甲,每个人的装备里不止一副盔甲。 在冲杀御敌时,我们会立断当下敌人有多大威胁,迅速而本能地,选择穿上哪一副盔甲保护自己。 带领读书的过程里,组内有同学问到:“解离是怎样一种心理防御,确切说它是怎样的状态呢?” 的确呢,事实上作为日常生活里、不曾经历过超巨大创伤、或不曾体验过剧烈情感的人来说,我们可能鲜少体会过解离是种什么状态。 要遇到怎样的战斗,才需要动辄到穿上“解离”这副盔甲呢? 那战斗一定超强悍且残酷,因为若不是那么大级别的战役,谁会想穿上“解离”这副盔壳呢?它是如此地厚重、滞缓、行动不便。 在回答读书会那位同学的问题前,恰好看了林奕含婚礼上演讲的文字稿——那位少女时期被老师性侵的天才作家。 在婚礼现场,她认真叙说了自己内心“生病”的过程。然后她介绍了多次体会到“解离”的感受—— “在休学前那阵子我常常发作解离……我喜欢用柏拉图的一句话来叙述它,就是灵肉对立。因为我肉体受到的创痛太大了,以至于我的灵魂要离开我的身体,我才能活下去。 我第一次解离是在十九岁的时候。我永远都记得我站在离住所不远的大马路上,好像突然醒了过来,那时候正下着滂沱大雨,我好像被大雨给淋醒了一样。 我低头看看自己,我的衣着很整齐,甚至仿佛打扮过,但我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的门,去了哪里,又做了些什么。 对我来说,解离的经验是比吃100颗止痛药,然后被推去加护病房里面洗胃还要痛苦的一个经验。 从中文系休学前几个月,我常常解离,还有另外一个症状是没办法识字。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荒谬。 对,但就是打开书我没有一个字看得懂。身为一个从小就如此爱慕、崇拜文字的人来说,是很挫折的一件事。” 她话语到这里时,阴郁、滞拙的痛苦以至于僵麻的感受,无声地、颤抖地落了下来。 那是明明凿凿,向无边暗夜里驶去的感觉。 南希在《精神分析诊断》里提到,“使用解离作防御机制的来访者们,多为自我催眠的高手。” 这并不是路人皆会的一种能力,需有“天赋”——他们在关系中的体验更敏感,想象力极丰富,有虚构的朋友、幻想的游戏、戏剧般变幻的情节…… 他们的内心像一棵两棵繁裕纷杂的葡萄藤,攀枝错节而掩语难言。 然而这个天赋也是天谴,最最令人悲伤的部分,是那些使用“解离”保护自己的孩子们,大多幼年经遇过被性侵、情感虐待、欺凌暴力、极残酷的折磨…… 一如林奕含所说:“我的肉体受到的创痛太大了,以至于我的灵魂要离开身体,才能活下去……” 嗯,灵肉对立…或者,灵肉分离… 解离有一切停滞、抽离的感觉。而解离的麻痹感,比隔离、隔绝要彻底、绝然得多。 小小孩子在被残忍对待时,被折磨的灵魂极度地恐惧、焦灼,真的无法安存在被凌虐的肉体里面,需把灵魂抽离出来,催眠自我这一切并没发生在自己身上。 被抽离出来的灵魂、那种僵麻的自体的感觉,漂浮在半空中,让自己可以旁观,看这幕降临在“非我”身上的灾难。 飘出来、灵肉分离的灵魂,像在灾难中死掉的星辰,没办法再发出光来。但是过往的光芒还在,在宇宙间流离失所,孤独奔走,没有着落。 这是“解离”的感觉。 所以可以体会到肉体迟缓,体会到思觉失调,体会到混乱无归,体会到不知身在何处,也不知去向何处。 严重时,好像在一个扭曲的、时间空间都诡谲变形的奇异世界。 解冻的悲伤 曾感受、听到鲜少的“解离”的体验,是拜工作所赐—— 手脚僵麻,咨询室的空间、时间甚至有些移置,内在的体验莫名地空泛漂离。甚至沉默中可能有的焦虑不安都如泡沫散掉了、不见了。 曾听过那样的描述解离的体验: 当窗外有浓烈的阳光照进来的时候,好像帮助静止的自己解冻了。 解冻了“解离”这个防御之后,都是很强烈的情感体验:比如悲伤、极大的恐惧、无助、愤怒。 那些悲伤、恐惧,是这个人曾遭遇巨大创伤后,无法承受,于是用解离将自己的感知和疼痛分开,把那份沉痛先搁置,在咨询中无意地投射给咨询师,潜意识、是希望咨询师能体会、知道这个人曾面对过什么样的灾难。 后来想到,爱伦坡在书中曾描绘过的一段文字,很类似从“解离”中稍解冻后的体验: “不知怎么回事——第一眼瞥见那座府邸,就有一种令人难受的哀伤渗入我的心灵。我心头有一种冰冷、低沉、需呕的感受——一种不可填补的阴郁无处不在……” 在日剧《DR.伦太郎》里,苍井优饰演的梦乃,是一名“解离性认同障碍”患者。 她被逼迫去做艺妓供养母亲和她的情人,母亲常年累月地骚扰,梦乃退缩到自己的壳里仍旧屏蔽不掉母亲要钱的电话。 母亲逼迫她用自己的肉体,去伺候令自己生厌的位高权重的男人,换取钱财填满母亲嗜赌、养情人等贪食无餍的欲望。 小时候被羞辱虐待、情感被漠离,但发觉生母是唯一可仰赖的人。对于梦乃来说,那么可怕、贪婪、混乱的母亲,是自己唯一能看到、摸到、可以依恋的人。 那些惯用解离防御机制的孩子们,童年期唯一可以信赖的客体,给他们造成了难以忍受的痛苦。 是如此地矛盾和屈辱——渴望着的、爱着的人,也是重创自己的人。 真正地被受苦者所使用的解离,尤其是较重度的解离,大抵比这难过一百倍。 他们其实不那么容易“醒”来,也不那么容易很快地让自己归位。 而归位后体会到的悲伤和痛苦,才是最最重要的部分。 因为穿越了那个悲伤,才知道——要多么恐惧、悲辛和无处可逃,才会关闭感知,给自己穿上“解离”那么沉重、木然的盔壳。 那是大到要麻痹自己才能活下去的灾难,也是许多个林奕含,曾遭遇过的“奥斯维辛集中营”。 像是解离发生的那一刻,天上的星辰熄灭了,死掉了,但残留在宇宙中的星光,还在很孤苦地飘荡着。 当你也体会到解离的那个人的悲伤后,哪怕只体会了一点点,也好似抓到了那些光。然后,也可以哪怕很艰难地,尝试让这些星光有个可以落脚的地方。 一起回归,共同体验 很多人问:“如果我不曾发生过那样的事件,是否我不能明白、理解那些发生过的人的感受。” 然而,即便我们不曾被性侵,不曾被亲人虐待,不曾被欺凌剥削,但不意味着我们不能理解被侵犯、被凌虐的感受。 不大认同人们去劝自己也劝别人,少看些负面新闻,少链接些负能量吧…… 一如南希自己都会在《诊断》中说,解离的症状很隐晦很有蒙蔽性,但比想象的要多,天知道有多少解离的人没有被世人察觉。 当我们拒绝跟这个世界发生的苦难有链接时,我们在使用情感隔离的方式,试图将自己放置在无菌无灾的环境里。 即便理解,那是因为人心之力不足承受,但仍觉得这种情感隔绝越来越多时,对这个世界来说,是不亚于“奥斯维辛集中营”的灾难。 跟他人的情感很遥远,就跟自己很遥远,也跟这个世界很遥远。 在《DR.伦太郎》里,梦乃凄苦无依时,对精神科医生伦太郎产生了情欲移情,她问伦太郎说:“我可以拥抱你吗?” 伦太郎的回答大致如此: “拥抱是零距离的,很亲密很亲密。但那样我就不能看到你了,不能更好地知道你发生了什么。我想站在你对面,想看着你的眼睛。那样,我可以映照你,理解你,感受你。” 这是心理咨询、心理治疗的距离,是镜映的距离,也是亲密但深情、可以清醒陪伴的距离。 因为那次解离的经验,经过专业受训,每当可能会遇到的、面前的人现在再次难以忍耐,把自己抽离陷入沉溺、停滞,空白的感受中时, 我会尝试理解,或许那可能是被唤起了痛苦的难以靠近的情感。 会尝试辨识,当对方无意识的节奏可以稍沉下去时,当那些苦难可以浮出一点时,或者可以跟Ta说: “我们可以慢慢来,一同来感受看看,我知道那太不容易了。过去是你独自承受、来帮助自己,但现在,我们是两个人。” 如此艰难,但荒凉之地大可以有人在。 注:
一般来说,会动用到解离这一盔甲的个体,往往是遭受过巨大创伤、或在某些情境里体验到强烈情感而难以承受……
1.解离症状最常发生在解离性认同障碍身上,即“多重人格障碍”(最近版本的DSM诊断将之称为“解离性认同障碍”)。也有非解离性认同障碍的人,因巨大创伤使用解离作为主要的心理防御机制。
2.人们在处理一些不稳定的情境时(如剧烈的情绪波动),往往会把解离作为首要适应机制(Nancy)。目前已有很多文献证明,解离现象在临床上比我们想象中更常见。